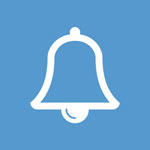台灣立法院再度爆發朝野立委激烈肢體衝突。20日,國民黨團預計排審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》、《憲法訴訟法》、《財政收支劃分法》等修正草案。此前,此三法案在提出之際即引發爭議,民進黨反對並批評國民黨提出的版本,認為國民黨意圖藉機護航不適任立委、癱瘓憲法法條,以及削弱中央可支配財源。
為表決此三項爭議法案,國民黨先於17日宣布開始輪班在立法院議場前守夜,以防三修正草案遭民進黨團杯葛。雖然民進黨成功進入議場且佔據主席台的消息一度振奮支持者,但態勢很快就翻轉。20日上午9時許,國民黨立委張智倫突破民進黨封鎖進入議場,隨後同黨立委魚貫而入,並與民進黨立委發生推擠、拉扯等衝突。
截至下午4時,在藍白聯手下,立法院已三讀通過選罷法修正案,未來民眾進行罷免連署時,不論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皆須附上身分證影本,若資料不清將視為無效連署。新法也增訂偽造連署最高可處5年徒刑或科處100萬元以下罰金。
下午5時,藍白黨團提案延長開會到凌晨12點並通過。晚間6時許,三讀通過憲訴法部分條文,第5條第1項,大法官未達15人時,總統應於2個月內補足提名。此外,參與評議的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10人,作成違憲宣告時,同意違憲宣告的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9人。
公民團體並提出5項訴求,包含「回復國會合議制民主秩序」、「退回選罷法、憲訴法、財劃法的3大惡法」、「國民黨總召傅崐萁下台」、「藍白莫作傅隨跟班」、「賴總統出面協調」,並譴責傅崐萁及其集團讓台灣民主倒退。經濟民主連合也聲明,公民團體將籌組律師團,協助各地罷免團體在憲法訴訟中提出法庭之友的意見書。
有關台灣立法院衝突的最新事態發展,請隨時留意後續更新。立即點擊連結,免費閱讀全文: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41220-whatsnew-taiwan-legislative-yuan-2